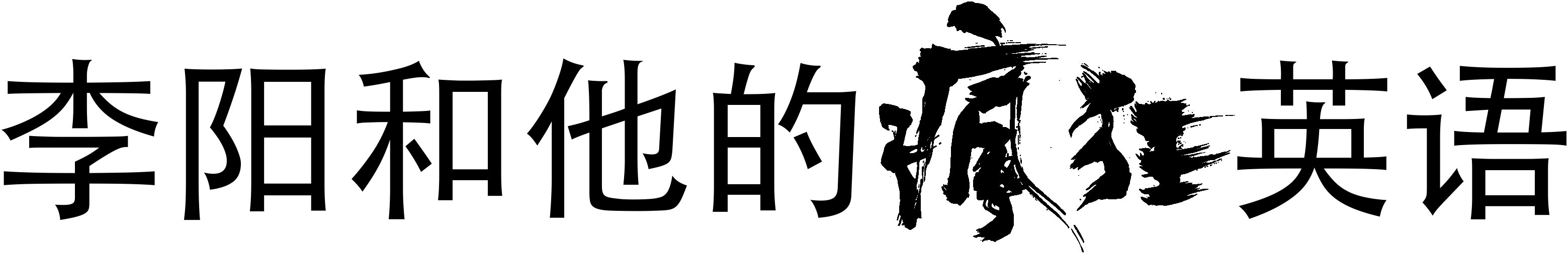疯狂英语:当张元遇见李阳
在学校我有下午去操场上跑步的习惯。去年冬天有一段日子,总看见一个人站在体育场的高高的看台上大嚷大叫,口里振振有辞的是一些英文短句,特立独行地面对着冬天的黄昏。后来我知道,这就是所谓“疯狂英语”,用李阳的话说,这是一种集“听说读写译”于一体的英语教学法,学习者只要顺着肢体的节奏,把胳膊高举,把手张大,把英语大声说出来,就能学好英语。
导演张元可以为李阳的疯狂英语拍一部同名的纪录片,我想完全是出于一种偶然。有一天,李阳公司的一个经理跑来找张元,说有一个人用疯狂的形式教英语,每次都有几万人跟他大声呐喊,挥舞手臂。
张元觉得,中国总有很多人一阵风似地去做事情,气功有很多人去做,传销也有很多人一下子参与进去。也曾有过学习的浪潮,比如高考,但他没想到学英语这样一件事,还有几万人同时跟着一个人手舞足蹈、疯狂地去做。中国有很多疯狂的经历,这样学英语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疯狂?李阳说,他是想让全世界了解中国,这个从前非常自卑的人发展到今天,成为一个彻底不要脸的人,他的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在他的纪录片《疯狂英语》里,张元把这些没有答案的疑问,融入于影像,呈现在我们眼前。

李阳之选择张元,我想也是一种偶然。他们看过张元给崔健拍的MTV,觉得那里边有一种英雄感,而李阳的这种行为本身就有摇滚的感觉,跟崔健的那种狂风暴雨式的力量很相似。于是他们选择张元,想让张元给李阳拍一个宣传片而不是纪录片。
后来我们看到的宣传片成为一部纪录片,和吴文光、段锦川、蒋樾等人的纪录片相比,张元的这部纪录片显然有太多的导演成分。张元说:“这部电影我给自己提的东西很多,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这部电影的导演和制片人,也做摄影师,所以我在拍摄的时候,虽然是一个纪录片,但在拍摄之前,经常给自己设计很多的草图,为这部电影整个的结构做很多很具体的设计。我是用电影35毫米胶片来拍这部纪录片,但我又不希望拍的素材太多,因为我对自己要有限制,我要限制自己到底要拍多少东西,所以说我对这部电影的构思就特别的精确。电影中的人物非常的疯狂,但是我希望我自己非常的冷静,我希望我非常冷静的去看这种疯狂,每一次李阳演讲的现场,人都非常的多,但我希望在人群当中,只有一个人是最冷静的,那就是我自己。”
电影中的重要段落一律是李阳在不同场景、面对不同对象传授他的疯狂英语。在六个月的时间里,张元拍摄了李阳在大庆铁人纪念馆对工人的演讲,在北京太庙和清华大学的演讲,在长城上带领解放军大喊英文,在JJ迪斯科和大学生边跳舞边大喊英文,在上海和股票市场的员工大喊英文,在湖南邵阳某希望小学破烂不堪的操场大喊英文……细心的话不难感觉得到,实地场景的选择和后期素材的剪接都是张元精心设计和编织的结果。
影片的开始,是李阳和剧组摄制人员在街头的雪地一连串地大喊“crazy”这个单词,不管多么滑稽,李阳的疯狂似乎具有如此的魔力,可以影响到他身边的每一个人,哪怕是作为第三人的观察者。作为导演的张元,这时候就更有必要保持他观察时的冷静和敏感,这是一个三者之间力量的微妙组合与平衡:张元和作为被观察者的李阳,作为演讲者的李阳和他的听众,张元和整个摄入他镜头里的人群。

当张元的这样一种观察者的身份确立以后,镜头里开始一连串交替出现形形色色的生动的人的面孔,他们的口里一律会有这样一句,“I love crazy”。平实的脸谱掩饰不住一种长期以来似乎是已经注入民族性格的腼腆的表情,可就是这样的脸谱,却在这样的一种偶然的触发之下,轻而易举地释放出内心里压抑已久的某些东西。李阳的宏旨正在于此,他要把英语作为这样一种契机,一种激发民族性格的契机,使对于英语的学习同时实现这样三重目的:发泄个人精力,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同时也为社会所需要。
这时候,李阳的雄心壮志已经很宏大。他把成功、学习和爱国主义这样的从个人到民族的种种自尊情绪揉合在一起。他说,“英语现在是沟通全世界的一个工具,一个掌握了英语的民族,它就掌握了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掌握了参与世界国际商业一体化的能力”,所以他觉得“学习英语已经不是一个语言问题,学习英语是生产力”。至于爱国主义,“爱国不是喊口号,不是唱爱国歌曲,爱国是知道自己的素质离国际化的要求还有很远,知道自己的国家还远远地落后于其他的国家,爱国不是一种自大,不是一种盲目,不是一种仇恨,不是恨日本人就是爱国”。他觉得“爱国的最好表现就是强大自己,说得更明白、更现实一点,爱国就是把英语学好。”
作为语言教学活动,在李阳的演讲里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些最简单、最基本不过的发音训练,这些训练离李阳自称的“让三亿中国人掌握英语”实际上相去甚远。学会以李阳的方式去读出几个单词、几个短句当然不叫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要学生开口大声讲英语,他把“三最口腔肌肉训练法”作为一种发明上升到理论高度,即“最大声、最快速、最清晰”,要锻造中国式肌肉……可是我们知道,英语教学中的口语突破,一直以来作为一种方法并不新鲜。
李阳在各种各样的场合里重复着他的上述言论,他的宏大主旨和他的实用内容,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空间里,以李阳的方式被散播。我们看到的影片几乎从头至尾,都在反复播放李阳全国各地的演讲,据统计,演讲的内容有10%左右几乎完全重复。更多时候我看到的李阳的演讲就是这样一种印象:高分贝的声浪响彻广场、响彻群山连绵、响彻中国的角角落落,整齐划一的手势和宣传材料在万头攒动中挥舞……
张元的影像所呈现到我眼前的疯狂英语,只余下一种苍白空虚的形式感。在纪录片里的李阳,没有展现他的私人生活空间,只是一个作为公众人物的平面的李阳,作为一个商业符号的李阳,而非一个真实的私人的李阳。无论是在铁人纪念馆高大的英雄塑像下,还是在太庙威严的殿宇前,还是在长城上,还是在卢沟桥头,在清华礼堂里,这些场景的选择无一不是刻意的、形式的、象征性的。

张元对于素材的组合、剪接是流畅而高明的。李阳在各地的演讲往往点到为止;当声浪响彻长城内外连绵群山以后,继而是恢复亘古不变的平静,山间偶尔有几声婉转鸟鸣;当声浪响彻某乡村小学以后,继而是贫苦山村老农面朝黄土,专心锄地、挑担的情景。无论是在声音还是在影像上,这样的组合、剪接都极富有画外的深意。影片好几处类似的过渡性段落,表达了张元对叙事节奏的良好控制,也让人看出,这部纪录片是一部经过精心思考和设计之后才投入拍摄的纪录片。
事实上李阳并不“疯狂”。作为一种纯粹的商业运作,李阳是思路清晰并且精明过人的。李阳说:“我不怕别人说我功利,商业社会谁被市场承认,谁就是对的。现在学英语不是只为了做学问,商人能用英语把生意谈下来,记者能完成采访任务就行。很简单,什么时候中国人能用英语赚世界的钱,就达到学英语的目的了。英语教学在亚洲绝对是一个庞大的产业,我恨不得培养一批人到越南、日本、韩国去教英语赚钱。”李阳疯狂英语之在全国的推广、风靡,绝对可以看作是一个商业品牌塑造成功的典型案例。
但是张元似乎并没有过多地着眼于疯狂英语的产业化运作过程,这可能是张元的某种妥协。当李阳和那个秃顶的老外在太庙前,面对着浩浩荡荡的人群签名售书时,当李阳马不停蹄地召集他的员工部署任务时,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疯狂英语的商业特征,仍然可以看到疯狂英语的商业包装要多于其实用内容。这是一个在商业社会下被孕育催生的巨型胎儿,李阳疯狂英语之所以能够在全国迅速扩张,有时候甚至得到了地方基层教育部门官员以及学校的参与、默许、认可,这些运作,其背后隐藏着怎样巨大的商业利益的驱动?这是影像以外带给我们的深层思考。
在张元的影像里,李阳是不是一个英语教学的专家?对此我不置可否。但是首先李阳一定是一个擅长于演讲的高手。很多场合里与其说李阳在展示他的英语教学心得,不如说是在展示他的演讲天才以及演讲学的心得。他提出学习英语时要有“不要脸”的勇气,那毋宁说是一种个性改造,毋宁说是在演讲的时候放下羞怯。李阳说:“我们有几句话很重要,‘重要的不是现在丢脸,而是未来会不会丢脸’,而且作为男人,作为人,应该‘喉咙管粗一点,把你的自尊咽下去’,不要让那些无聊的面子、可怕的那一点点自尊扰乱了你的成长。”
李阳还认为:“人生的缺陷都来自于内心的缺陷。一旦你的心理很健康的时候,一旦心里没有界限的时候,那人生将没有界限。你将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常人感到害羞的你一点也不感到害羞,常人感到恐惧的你不会感到恐惧,所以一旦进入疯狂的状态,一旦实现这一步的时候,你已经站在世界的巅峰。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对生命的完全控制,对社会、对环境的完全的控制,‘坏事都是好事’,你最大的缺点是背后隐藏着巨大的能量,一旦突破,你一生中你认为是缺点的东西将会变成可以撼动世界的优点。”
当李阳站在看台上阐述他的三大理想,一是要让三亿中国人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二是要让中国之声,、中国产品、中国文化响彻世界;三是要让三亿外国人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张元的镜头一次次给李阳的形象以高大全的仰拍,我相信台下的许多人一定都会被李阳的这些那些的想法激动、鼓舞着。有时候,三台摄影机同时对着李阳,其中有一部是顾长卫执机的,为中央电视台拍摄《知识改变命运》,李阳说,那天由于灯太多,把天花板都烤着了。
以英语教学为契机,李阳以他的演讲完成了对于他自我的英雄形象的缔造。“现代年轻人需要偶像,我的经历对他们很有示范意义。”李阳不否认自己的偶像作用。李阳甚至直说,他李阳就是等于英雄加英语二者之合。而媒体这时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编织的作用。在一个缺乏神话的时代编织神话,编织偶像,也许我们的内心无意识的深层还积淀有某种偶像崇拜的情结;当我们从各自私人生活的空间汇聚到一个开放式的空间里,我们缺乏有意识有组织的理性经验;当学习成为一种集体的同步行为,我们觉得新鲜。于是我们被李阳激动着。

张元说,他一直对参与人多的事情感兴趣,李阳的有趣在于他的故事非常荒诞。但是当张元遇见李阳,张元的影像事实上是一种暧昧的呈现,张元的态度是暧昧的,不置可否的。张元说,他喜欢观察这个事件中所呈现的社会和人的状态,也许对于李阳疯狂英语这一事件本身,作为一个敏感于文化风向的电影导演,作为一部纪录片的作者,他的最好的姿态,莫过于观察。
(via 网易娱乐)